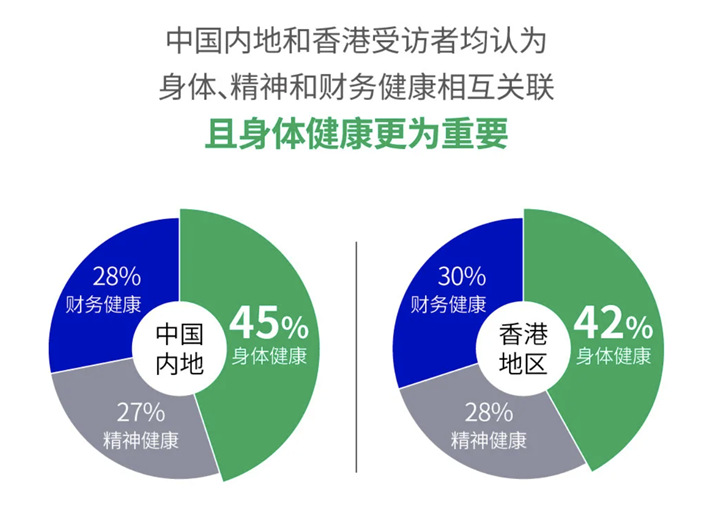养老保险降费应与其他改革同步
2014年中央政府表示将适时适度降低社会保险费率,2015年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费率分别下调了1%、0.25%和0.5%,总共下降1.75%,相对40%的费率而言,远不能缓解劳动力成本高引起的疼痛。
2015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降低社会保险费以降低企业负担的思路。
在我看来,除了养老保险,其他险种降无可降,而养老保险降低费率必须与其他改革同步,如果只是简单降费,会使制度与其“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目标背道而驰。
高费率引发“公地悲剧”
应该看到,社会保险高费率已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
近些年工资增长较快,社保的成本也一同增长。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跟踪调查表明,企业连续多年将“税费过重”列为影响自身发展的重要原因。出于降低用工成本的考虑,一些企业正考虑用机器替代劳动力,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富士康的“百万机器人”计划。从经济的角度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不是坏事,但如果引发就业不足,则是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评价一个社会保障制度的标准之一是它的覆盖率,因为覆盖率是重要的平等指标,即人们是否有平等权利参加社保制度。
社会保险虽然是强制性制度,但非农就业人口的参保率,尤其是农民的参保率还远远未达到理想状态。人们不参保的原因很多,其中高费率是重要的原因。
2014年底,在2.7亿农民工中,参加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刚过5000万人,其他险种的参保率更低。农民工的保障是一个大问题,也是新型城镇化即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大难题。
高费率还会引发大量的道德风险和断保问题,最后导致制度保费收入减少,并会降低有效参保率,引发典型的“公地悲剧”,即缴费时大家都想少缴费,享受待遇时人人都想多得福利。
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中单位就业人员的费率为28%,其中企业负担20%的费率,保费进入社会统筹,个人负担8%的费率,保费进入个人账户;企业职工的缴费基数是社会平均工资的60%-300%,获得养老金资格的缴费年限为15年;领取养老金的法定年龄是女性工人50岁,女性干部55岁,男性60岁。为了扩大覆盖面,2005年国家出台政策规定,灵活就业人口、个体工商户以20%的费率加入社会保险,其中12%进入社会统筹,8%进入个人账户,但其缴费基数为社会平均工资,获取养老金资格的缴费年限、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和计发办法与企业参保人相同。
中国的工资和劳动收入不透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高费率引发的第一个道德风险是企业少报瞒报工资基数,少报职工人数,非正规就业者的收入基数更是不透明。许多研究认为,实际缴费基数大约为应缴费基数的70%左右。第二个道德风险是一些企业鼓励员工按非正规就业参保,以享受低费率。结果是一些地方近一半的参保人以60%的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参保,一些地方近一半的参保人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保。这显然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另外,高费率还是断保的重要原因。所有这些问题最后都会减少制度的收入,也会影响到受益人的保障水平。
道德风险进一步造成了保费负担不公和法治恶化。
一部分企业和个人严格遵守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认真履行相关的义务,一部分人通过各种办法规避或者缩小费税的责任,引发了社会保险负担的不公平。社会保险应该具有再分配的功能,但这种再分配必须是在成员公平负担义务的情况下发生。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却是遵纪守法者向义务规避者再分配;薪水记录完整的中等收入者向部分收入不透明的高收入者再分配。这些现象挑战的是政府通过社会保险制度干预社会生活的有效性,是社会保险制度的性质所不允许的。
道德风险的发生恶化了法治环境,也让部分缴费主体因逃避缴费义务而惴惴不安。
养老保险领域的道德风险严重影响到社会保险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影响到人们对社会保险制度的信心,以致有人呼吁干脆用个人账户取代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综上所述,高费率引起的问题不只是缴费主体的负担加重,同时也是低收入者进入社会保险的障碍,还是道德风险的诱因,进而危及到社会保险的合理性。
所以,降低费率不仅有利于减轻缴费主体的负担,也有利于提高参保率,有利于控制逃费漏费的道德风险,提高社会保险制度有效的再分配功能。
养老保险制度经过十几年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仍然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此次中央提出适时适度降低费率是绝对正确和受欢迎的,我们应该利用这一时间窗口,对养老保险制度做一次全面的检视和思考。笔者就此提出如下建议。
政府明确承担转制成本
当下在职的一代人负担高费率的部分原因来自于经济体制转型。
上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改革,数以千万计的国有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或者以较少的工作年限进入到退休状态,或者以趸缴保费的形式取得领取养老金的资格后不再缴费,用这样一些措施部分补偿职工在改革中的损失。
这些措施使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比大大高于人口赡养比,最后体现在高费率中。
这些转制成不应该由当下在职的一代人来负担,而应该由政府来负担。政府应该通过立法明确这部分责任。不然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养老保险费率如此高,保障水平如此低,还会收支不平衡。
建立二元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在现有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可建立国民养老保险(借用日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名称)。
前者以单位就业人口和中高收入的非单位就业人口为主要保障对象,在降低当前费率的情况下,提高其他条件,参保人尽较高的义务并可获得较高的养老金,即“高进高出”,平滑中等收入者的终生收入;后者以非正规就业者为主要保障对象,以较低的费率和较低的资格条件参保和退休,政府给予制度适当补贴,“低进低出”,平滑低收入者的终生收入。该制度是用政府的一般税收完成社会养老保险的再分配,而不是目前的中等收入者向低收入和搭便车者的再分配。
笔者早前的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二元结构,用一个统一的制度为其提供养老保险,“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三者之间是矛盾的。
为了广覆盖,除了费率高之外,其他参加制度的门槛条件和获取养老金的资格条件过低。如果一个人以较低条件参保则达不到“保基本”的目标,如果制度补贴他们以“保基本”,则制度不可持续。尽管在一个制度下设计了两个费率和两个费基,尽管从“保基本”和可持续的角度看制度的条件是低的,但仍然有许多人没有加入该制度,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对他们而言,养老保险的门槛条件和资格条件仍然太高。
我们的早期研究还发现,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制度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是不经济的,是高费率低保障的原因之一。
许多年来,主流舆论一直在推动职工养老保险向“统一”的方向发展,从管理的角度和收入平等(不等于公平)的角度看,这一方向是理想的,但越是“统一”离同时达成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三个目标距离越远。
一个制度下,照顾了中等收入者的“保基本”则低收入者进不来,相反照顾了低收入者则中等收入者达不到“保基本”,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设计为搭便车者留下了空间。
不同的人群参加不同的制度被称为“碎片化”,碎片化在中国是饱受指责的。而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碎片化可能是比较现实的选择,它可以使更多的人有与自己的就业收入和社保贡献相当的养老金收入,而不是一部分人被排斥在外,而只是制度内的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制度。也许有人说,中国的居民养老保险可以覆盖非正规就业人口,这是一种选择,但是居民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是极其有限的,我们应该尽可能鼓励就业者为养老多做准备而不是相反。
纵观国际经验,主张“统一”论者一般会以美国的社会养老保险为例。但我们必须知道,美国1935年建立统一社会养老保险之时已于20年前完成了工业化,美国也从来没有小农业生产者,它的农民是农场主。相反,更多的是欧洲大陆、日本等国家保留了碎片化的社会保险制度,拉美国家为了扩大覆盖面也建立了碎片化的制度。
我无意说“碎片”的制度比“统一”的制度好,只是想说养老保险碎片的制度可能更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统账”分离
个人账户设立的意愿是非常善良的,但实践证明在现阶段的中国没有办法让该制度比社会统筹做得更有效、更经济。
上世纪90年代设计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时认为,该制度有利于参保和缴费的激励,也有利于基金积累以减轻未来的缴费负担。
现在看来全然不是这样,由于是公共账户和个人账户的混合,政府责任和个人的责任的边界不清楚,没有人关心个人账户的积累,参保人关心养老金的多寡,而不是从个人账户拿多少钱。
至于说到积累制度,问题更是多多。第一个难题是个人账户要不要做实,如果做实的话需要大量的转制成本。由于改制时没有明确计算这个成本,现在它成了一笔糊涂账。第二个难题是做实后要不要市场化运营,不市场化运营收益率必低,假如市场化运营,谁敢为个人资产的投资亏损担责?
现实的情况是,由于没有积累或者是没有投资收益,制度只能给个人账户这笔长期资金记一年期银行利息率。制度成立以来,一年期银行利息率不到3%,而同期工资年均增长率为14%左右,相对于工资水平,个人账户积累越来越小,这是退休金替代率下降的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目前个人账户的发展进退维谷。
最近,将个人账户做成名义账户的想法受到重视,因为名义账户制度下政府不需要转制成本,也不需要担心资金保增增值的问题。
所谓名义账户制度就是现收现付加个人账户,即在职一代的缴费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制度将缴费及名义的利率记录在个人账户上,因为账户上并没有资产积累,因而称之为名义账户。
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由于没有基金积累,其实就是一个名义账户。
名义账户的问题是,利息率如何记录。如果利息低于工资增长率,则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下降;如果利率等于工资增长率,则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工资增长率一定不会低(因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意味着7%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工资增长率正常的情况下会高于经济增长率)。记较高的利率则意味着制度的负债必然高,下一代的负担必然重,而中国的老龄化在加速,下一代不堪重负时制度会破产。
降费率与扩费基同步进行
扩大费基包括提高最低缴费工资基数、延长缴费年限和逐步提高退休年龄。
除了“统账分离”可以降低8%的费率外,费率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目前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比为3∶1,即三个在职人员赡养一个退休人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为社会平均工资的43%左右。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调整缴费工资基数、缴费年限和退休年龄三个参量,使得制度三个在职人员在平均水平上按社会平均工资的100%缴费,只要承担15%的费率就可以使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5%,且制度是长期可持续的。
目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征收与支出状况不容乐观,其他条件不变时,降费率必然减少保费收入,制度可持续发展堪忧。
从个人的角度看,现行的养老金计发办法中包含了浓厚的“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成分,如果不通过提高缴费基数、延长缴费年限、提高退休年龄等措施来扩大缴费的基数,意味着个人养老金水平的下降。
所以无论是从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参保人的养老金待遇看,降低费率的同时需要通过提高缴费工资基数、提高缴费年限和提高退休年龄等措施来扩大费基,以保证在降低费率的情况下,实现个人的“保基本”和制度的可持续。
降费率与扩费基同步并不是数字游戏,更不是零和游戏。
降费率扩费基有利于减轻收入透明且严格守法的中等收入者的负担,因为扩费基不会增加他们的负担而降费率会减轻他们的负担。降低费率是为了降低养老保险进入的门槛,在工资水平一定时可以让更多的人有能力加入进来,以提高制度的覆盖率;提高缴费工资的基数是提高了进入制度的门槛,会对提高覆盖率起反向的作用,但是由于缴费工资基数在计发基础养老金时起很重要的权重作用,所以提高缴费工资基数会提高个人养老金的水平;提高缴费年限可以使参保人在较长时间内均衡缴费负担而不是在15年内承担较高的费率,就像还房贷,同样的贷款额度,如果一个人选择在短时间还清,则每个月的月供会很高,如果他的收入不高,想减轻还贷款的压力,他可能会选择更长的还贷款期限。
另外,提高退休年龄会对制度的收入和支出起双重的作用,也会对个人养老金水平的提高起作用。
有论者不是从参保人的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来考虑,只要涉及社会保险制度收支不平衡时,会简单开处方,让政府出售国有企业股权以弥补制度的收支缺口。政府对制度改革时“老人”和“中人”的补偿是合情合理的。这两代人当年的退休金权益是以低工资和隐形税换取的,所以政府需要明确这部分责任并进行补偿。
除此之外,我们提变现国有资产弥补社会保险需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国有企业是全民的,而社会保险则是参保人的,用全民的财富补助部分人口是缺乏理论支持的。
同时,如果我们不扩大费基,仅仅盯着国有企业的存量财富,对后代也是不公平的。当老龄化达到峰值以后负担缴费的一代又一代是不堪重负的,我们现在可以指望卖国企,他们能指望什么?
总之,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尤其是降低养老保险的费率是正确的,但制度的结构性调整和参量调整必须与降低费率同步进行。